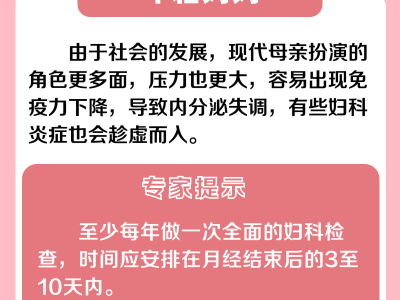小賡是初一男生,成績出色,遵規守紀,是老師同學都很喜歡的“好學生”。每節心理課上,他都認真專注,積極參與課堂互動,但我總是覺得他的積極顯得不太自然,有那么一點兒“刻意”。有幾次下課時,他主動來找我聊幾句,我也發現他欲言又止。
這天,我接到了他班主任的緊急求助電話,說小賡在歷史課上情緒失控了。起因是他沒有按老師的要求做規定任務,而是偷偷寫政治作業。歷史老師看到后制止了他,提醒他歷史課任務下課要交,讓他課后再完成政治作業。同學們都覺得老師的語言并沒有太嚴厲或者過激,只是正常的提醒。結果小賡就開始控制不住地笑,接著又哭,就這樣又哭又笑地折騰了很長時間也停不下來,搞得老師同學都莫名其妙。于是歷史老師找來班主任,班主任將小賡從課堂上帶出來,問他原因,他泣不成聲說不出所以然,只說想找心理老師聊聊。
在咨詢室坐下后,我一邊給他遞紙巾,一邊帶他做呼吸、轉頭等迷走神經系統的訓練,讓他感覺到當下自己是安全的。小賡的情緒逐漸平復下來,呼吸也平穩了,于是給我講述剛才的情形。他說他也覺得老師只是常規提醒,但不知道為什么,那一刻就覺得很好笑,但又知道笑很不合時宜,好像要挑釁老師似的,于是就憋著。但下一刻,又有委屈涌上來,最后終于憋不住,變成了又哭又笑。
我問他之前是否也曾有這樣糾結和失控的經歷,他立刻說:“老師,確實有的,這個跟我的經歷有關。”
于是,小賡開始給我講述他的成長故事。在小賡3歲時,父母就離婚了,小賡跟著媽媽和姥姥姥爺一起生活。自離婚之后,爸爸就很少出現在小賡的生活里,直到五六年級,爸爸才開始有規律地一年來看小賡一兩次,帶他出去玩,一起吃飯等等。
媽媽總說爸爸是個很虛偽的人,講述爸爸的種種不好。當爸爸回來看他時,最初他內心是很拒絕的。隨著慢慢長大,小賡發現爸爸并不像媽媽說的那樣虛偽和不堪,對他也真心誠意、關愛有加。回到媽媽身邊時,小賡還是想認同媽媽,于是內心就很矛盾很糾結。
“現在讓你矛盾和糾結的點,并不是該相信自己還是相信媽媽,而是如何能既向媽媽表達自己的觀點,又不得罪媽媽。對嗎?”我嘗試進一步澄清小賡的感受。
“太對了,老師。”小賡眼中閃過光亮,是那種被看到被理解的喜悅。
小賡告訴我,媽媽的情緒很不穩定,姥姥的情緒也不穩定,姥爺只是表面穩定,但已經被確診為焦慮癥。自己似乎也被遺傳了情緒不穩定,但他有自己的應對策略,大多數時候,他都會“逃避情緒”,所以看起來好像是穩定的。他想嘗試改變媽媽對爸爸的刻板印象,又擔心會“忤逆”媽媽,畢竟他從小的人設就是“聽話懂事”,只有表現“乖巧”才能讓家人情緒更穩定。
“小賡,你說的這些我聽明白了,似乎你們家的人彼此互動的模式,就是用情緒互相淹沒。我的感覺對嗎?”我問他。
小賡笑了:“確實是這樣,老師。”
“你怎么看待家庭成員彼此之間的界限感呢?如果0分是非常模糊,不分彼此;10分是界限清晰,責任明確。你覺得你們家人的界限值是幾分呢?”
“老師,我覺得我們家人界限感確實不清晰,也就5分吧。但這樣也挺正常吧,不然劃清界限也太絕情了,不像一家人了。”小賡說。
“哦,原來你是這么理解界限感的。”我笑了,“界限感并不是劃清界限、冷眼相對,而是一家人各自端自己的飯碗、挑自己的擔子。有清晰的界限感,就可以保證家庭成員都能各司其職,處理自己該處理的事情,承擔屬于自己的責任。而不是總想著去拯救別人,也不是把改變現狀的希望寄托在別人身上。”
“老師,我有點兒明白了。我媽總說,如果我學習更好了,她就會更開心,實際上這是不對的?”小賡問我。
“也不能說不對,你學習好,媽媽為你開心,這是合情合理的。但是,媽媽更應該學會管理自己的情緒,而不是把調整情緒的責任推卸給你。畢竟就算你學習更好了,她的情緒管理能力并不會得到改善。但如果媽媽能夠看到自己的問題,有意識地去提升自己的情緒穩定性,你會因為她而變得更好。同樣,如果在媽媽情緒爆發的時候,你能夠很好地保持穩定,而不是亂了陣腳,媽媽也會因為你的穩定而更快平復,就像你剛到咨詢室來我帶你做的訓練一樣。如果能做到這些,一家人才是真正地同向同行,而不是彼此消耗。”
“老師我明白問題在哪兒了,我確實總是想著怎樣讓媽媽好起來,甚至一味地討好媽媽,想以此來平復媽媽的情緒,從沒想過怎樣讓自己更好一些。我表面的穩定,只是習慣性地壓抑自己的情緒。”小賡說。
“你對自己的覺察,面對自己不足的勇氣,都是很值得敬佩的,為你點贊。”我發自內心地向他表達了欣賞。
小賡有點兒不好意思,但臉上有著掩飾不住的欣喜:“老師,其實我早就想來找您好好聊聊,但一直在糾結和猶豫,也不知從何說起。今天這次情緒失控給了我一個契機,我突然明白了自己該怎么做。也突然覺得,我大可不必活得那么謹慎和糾結,心里感覺很亮堂。”
“也謝謝你的信任,愿意把這些故事講給我聽。以后有需要,歡迎你再來找我。”